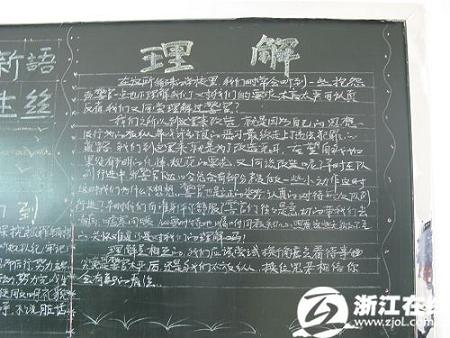艾滋毒品映照人生百态 民警被抓破脸后怕(图)
门禁系统隔开了两个世界
4号楼住了群神秘的男人 艾滋病和毒品映照出人生A面B面
2003年12月8日,浙江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正式收治了浙江第一名吸毒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今,已收容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200多人次。
2003年12月起,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劳教民警开始壮胆子、扛担子,从惧怕到亲和,从单一严管到人性化管理。这些与艾滋病患者走得最近的男人们,付出了许多心血。
7年来,围绕艾滋病、戒毒,这些男人在4号楼里发生了什么?
阳光下,杭州城北。浙江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院子里,一群中青年男人在操场上出操。
他们留给了我一群充满生气的背影。烈日把影子拉得很长。集合哨响,他们迅速靠拢,阴影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小。
对于他们而言,正因为人生的另一段相似的阴影经历而聚合在这里——吸过毒,患了艾滋病。
在这里,阴影逐渐从斜长变短。
这65位男人,是浙江某强制隔离戒毒所艾滋病专管中队学员。国际禁毒日前夕,浙江在线记者获准进入这一戒毒所,与他们面对面谈话,这也是4号楼首次对媒体开放。
我承认,虽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见到他们,我还是会慌乱,紧张,甚至有点却步,当话闸子打开,让他们的倾诉与记者倾听成为一种温和的交流方式后,一切都变得自然。所谓的“身份”意识慢慢退却。
很多时候,因为陌生,或者拒绝,我们害怕,进而歧视。
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只在意他们的身份,而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倾听“艾滋病人”、“吸毒者”身份的来历。
神秘的“4号楼”
4号楼,没有想象的神秘。
4号楼很不起眼。跨进紧锁的铁门,穿越塑胶的羽毛球操场,右拐,再经过习艺培训间,一座5层的小楼就是了。
4号楼也有名字,叫“康复楼”。是全省唯一收治男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的专管中队。
电话是艾滋病戒毒人员与外界维系的纽带
所有强制戒毒劳教学员都会在这里短期停留
李孟春所长说:“戒毒人员送到所里后,首先进行艾滋病初筛检测,对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戒毒人员,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本人告知。每年还邀请疾控中心专家给艾滋病戒毒人员举办艾滋病防治专题讲座,组织医务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发放一些慰问品。”
除指定的管教民警和戒毒人员之外的任何人,很难获准进入。
所有强制戒毒劳教学员,一般都要在这栋楼进行短期的停留。所有落所新来的,都要在这里接受教育后重新编队,进入常规中队。
而有一部分人不会这么幸运,他们是学员当中最不守纪律,常常不服管教的人,会从常规中队出来,投放到这里重新编入严管中队。
这两队人马,一是因为“新来的”,二是因为“老油条”,而被许多学员所注目,除了用作谈资之外,他们不愿接近。实际上,他们也没有接近的机会,这栋楼,单独管理,单独操练,单独劳动,单独作息。
严管队在三楼,手上有着刺青的学员刘东(化名)指指头顶,说,4楼的人才可怕。
4号楼4楼,颇为神秘。5楼是空着,为了腾出地方接待可能更多的艾滋病强戒劳教学员的到来。作为全省唯一接受男性艾滋病戒毒学员的地方,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做了充分的准备。
事实上,之前,这里一度也收押了女性艾滋病学员,因为管理的尴尬而转移到另一监所。4楼65人,是历来人数最多的,而马上,又将有一批转运来的5名患者到所。
从2003年11月至今,4号楼已经收教艾滋病强制戒毒隔离人员200多人次。
他们集中于外省籍,浙江本省人仅仅两人。西南的贵州人占了半壁,其次是云南、四川还有新疆。
在毒品猖獗的西南,他们在当地就开始了吸毒史。
政委罗爱民描述,这里的戒毒者一般遵循的规律是“外省籍在浙打工人员——不良的生活习惯——开始吸毒——感染了艾滋病”。
我省研究毒品犯罪的一位警界资深人士称,西南在浙的涉毒犯罪严重,而且云贵等省份的吸毒者在浙“潜伏者”众。
自办的黑板报
一套门禁系统隔开了两个世界
戒毒者的活动半径不超过10米,4楼宿舍和电视房,1楼的生产间和教室,再就是门口标准的篮球场。吃饭,有食堂师傅会专门一车车拉来。用餐后,所有饭菜容器将送到收容点,单独消毒保管,排泄物也都每日进行及时消毒处理,所有生活用品和理发工具专人专用。
结实的门禁系统将长排生活区与楼梯隔开,坐在门口的值班室,目光所及直到尽头。值班室里的监控操作台上,每一个探头都忠诚地记录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王警官,曾经艾滋病专管中队中队长,如今是分管艾滋病中队的副大队长。掏出磁芯门牌开门,带着记者走进去。右边是谈话室,一旦有心理问题,便可以在这里接受具有国家心理咨询师资质的劳教民警的谈话。
紧挨着的是电视室。每天晚上7点,雷打不动地集体按时收看“新闻联播”。
407室有几位值日学员在谈天,看到王警官,迅速起立报告。他们区别于常规中队,全部住下铺,因为怕上铺意外跌落受伤出血。被子整齐地叠成了方块豆腐。
一楼,工作间。
看到有陌生人突然进入教室,他们都把目光朝向记者,手头上的习艺培训活儿停下,记者有点不好意思了。
在此之前,这里禁止对媒体开放。他们互相嘀咕着,这是谁来了?
出乎记者的意料,他们大多并不虚弱,没有羸弱到气若游丝,也没有枯瘦如柴,相反,记者的身形在队伍里算是十分瘦弱的。
李孟春说,艾滋病的潜伏期长至12年以上,现在接收的戒毒人员一般都在感染5年之内。没有病发,他们和正常人一样,但免疫力相对弱一点。
但如果病发,他们就像点蜡烛一样,一烧完,生命终结。
混江湖的他,厌倦了江湖
东奇(化名)喜欢称自己是蜡烛,他每天睁开眼睛都会自嘲:哦,蜡烛还没有灭。
3日,是他农历生日,这位浙江南部某县的青年的而立之年。
一身江湖味,“玩过多少女人”、“偶尔打K粉”、“跟着老大看场子、抢地盘”,“开店生意不好就关了”,上述记忆碎片在他嘴里平淡无奇,犹如咀嚼过的青菜梗子,构成了他30年人生之前的主要回忆。
在这个盛产富翁的南部城市,东奇的家境也算殷实。读到初一,一次一如既往的考试过后,他撕毁了试卷,跑到父亲跟前,说“我不读书了,我想早点学做生意!”
排行老三的他最受父母疼爱,他的父亲可能至今为他做过的决定懊悔不已。
最害怕晚上熄灯那一刹:明天,我会醒来吗?
东奇开始混“江湖”。现在在戒毒所,他也最爱看一些武侠小说。
“我喜欢跟比自己成熟的人玩在一起。”他叫隔壁村一个朋友“大哥”,如同港片里的画面,在一个破烂而隐秘的房间里,他摊开锡箔,拿着“大哥”的ZIPPO打火机,幽幽地点燃了第一口海洛因。
和所有64名艾滋病感染吸毒者一样,他的解释是因为好奇。
经过初次“头重重的,想呕吐”的吸毒体验之后,他着上了海洛因的道。
跟大哥,当老大。抢地盘,看场子,收入不菲。但开销也大。“做老大的,总得给弟兄们分到好处,比如,做一单10万,得分个5、6万给弟兄们快活。”
所谓的快活,是开始在KTV、夜总会里喝酒、打K粉,寻找女人。
“我从来不找街头洗头房里的女人,一般跟一些酒吧里的女人一起玩,大家有感觉了就过夜了,从来不戴套。”在东奇的感觉中,这些女人都很“高档”,怎么可能会有艾滋病,连性病的顾虑都没有。
“我不知道自己玩过多少女人。”说这句话,东奇没有半点炫耀,双手握紧,眼睛望着窗外,因为从未针孔注射过毒品,东奇认定,自己是通过不洁的性交感染上的,究竟是谁?
“就等于在热锅里寻一只6条腿蚂蚁,不确定。因为每一只蚂蚁,都是6条腿。”东奇状态很好,具有江湖的“不怕死”气质,乐观,不忘记跟记者这样打趣。
戒毒人员都住下铺,以免意外摔伤
他们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更是特殊的病人
这个“江湖”让他身陷艾滋病之扰,他开始厌倦了这个江湖。
如果前几次进强制戒毒隔离劳教所,还有出去复吸的可能。这次,他坚决地说了“不”字。他清楚自己的身体,虽然艾滋病毒在体内潜伏最多不超过3年,但他决意停止毒品,“吸下去,等于更快死。”
因为免疫能力较常人弱,东奇在戒毒隔离期间数次感冒,常人不吃药都能好,他吃了药也好得慢。他很感谢这里的劳教民警,在全部公费医疗的环境里,获得了较好的救治。
省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政委罗爱民说:“现在的执法理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艾滋病戒毒人员不仅是‘违法者’,也是‘受害者’,同样是‘病人’,而且是特殊的病人。特殊病人的双重意义在于,他们吸毒,经常幻觉,脑损伤,有精神疾病,另外,他们是艾滋病感染者。”
想起小时候过生日妈妈做的红烧肉
这里作息时间与外面不同, 4号楼一天的生活——
7点半起床,吃过早饭后做一些轻微的习艺性劳动,午饭后安排午休,下午进行适度身体训练和体育运动,晚饭后自由活动,可以下下棋、看看书什么的, 7点收看新闻联播,9点熄灯。
中午10点半吃饭,这天,他特意打了份红烧肉,因为小时候过生日,妈妈会给他做红烧肉。
应该还有7个月,东奇将解除劳教,回家是他最想的事情。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情,他说要陪着一直爱自己的女友去做检查,如果有,就“拿起男人的气概”告诉女友,一起过下去,我负责到底。
如果没有感染上,东奇说,会跟她“拜拜”。
“我不会吸毒,但也许还会玩女人,风花雪月不可能避免,但至少,我会戴上套子。”东奇面对浙江在线记者抛出的“出去后,你会不会将艾滋病毒再传染给别人?”这个似乎敏感而直接的提问后,飞快回答。
“人心是肉长的,我即使在江湖里混,但不会主动去害人,再说,传染艾滋病毒也是犯法。”
东奇跟记者握了握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拜托记者隐去真实城市和姓名,起身离开,回到他那个40公分长的习艺培训操作台去。
东奇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伙食不错,有肉吃。一些简单的习艺培训打发了无聊的时间,阅览室的书籍发到每人的手上,轮流交换着看。
他最害怕每晚的熄灯那一刻,望着偶有光亮的窗外,他担心,明天还会醒来吗?
他常常面对墙上的福字陷入沉思
有过同样的担心的还有岳山(化名)。
岳山把每天的乐趣放在了习艺培训上。在精巧的手工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成就感的满足。
郭晓明副所长告诉记者,所有男性患有艾滋病的戒毒人员,全部被送到这里,实行单独管理、单独操练、单独劳动、单独作息。

平时会进行习艺培训
听到那个消息,他觉得“人生完了”
之前,岳山的成就感在于幻梦之中,一针海洛因进入静脉,血脉扩张,上升到颅顶,那种飘飘然的快感让自己沉醉并不能自拔。
34岁的岳山,已经像43岁的中年人一样憔悴。眼睛无神,嘴唇尖薄得令人害怕。
他至今未婚,溺爱他的父母和姐姐只能一次一次得用钱来满足他唯一的快感。
吸毒后,他离开了贵州贵阳一家大型集团公司的驾驶岗位,到处打工,支撑那每次一袋300克的白粉。
岳山形容去年那一刻,是“噩耗”。
在经过一段时间强戒以后,他决定离开贵阳,听说义乌有钱挣,就坐上火车往东。在经过一个月的零工漂泊之后,很快,他找到了一份制作饰品的活。
他请记者相信,自己选择一个新环境,确实是为了脱离毒瘾环境,但在义乌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通过老乡,他打听到在义乌机场北面的村子里,有“货”。
似乎嗅到了那熟悉的诱人的香味,他熟门熟道地进入机场背面的那个村庄,这里像极了著名漫画大师弗兰克?米勒之笔下的《罪恶之城》,似乎永远没有白天,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坐在暗处,放肆地用鼻子吸食,用别人递来的共用针孔扎入身体,体验久违的快感。
也是在村里,他被派出所民警抓捕,随即送往金华强戒所。
去年7月13日,他所说的“噩耗”到来。民警告诉他,“你被确诊患有艾滋病”。
一个月的错愕之后,他被带到了这里。该所一位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称,艾滋病学员一经检测并得知自己的确诊结果后,往往会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通常会出现否认、怨恨、妥协、抑郁和接受等阶段。
朋友的离弃、亲人的决裂,已经因为吸毒造成,而感染艾滋病,“使原本就脆弱的心冰凉到了零点”,岳山承认,那个时候,他怀着仇恨与抵触的心理面对劳教民警。
艾滋病专管中队倪中队长很熟悉这位一进来时语言孤僻、行为怪异的贵州人。为了治病救人,他和干警自然不厌其烦地开导谈心。
岳山的心理冰山开始融化。一次交谈中,他一改常态主动地问管教民警:“为什么你们如此关心我,我是艾滋病人。”
民警回答,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你也是。
戒毒所向其家人隐瞒了他的艾滋病情况,以便他回归社会时不被歧视,没有更大的心理负担。
在这里,重新找到了单纯的快乐
在4号楼,岳山到底过得如何?
岳山在这里,麻木的情感开始升温。
413,他的房间。床头墙面贴有福字,这个福字是过年戒毒所联欢时留下来的,他说,这是为所有同伴祈福。蜷缩在床上的时候,他会经常看着这个福字发呆。
在这里的,之前都在公安部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强戒,毒瘾是不大会犯的,但艾滋病的心结如何去解开?
岳山说,这里对于外界是神秘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一切似乎与“脚镣”、“体罚”有关,但他想告诉怀疑论者,这里充满了温情,而且可以改变你对人生观的判断。
许多刚来这里的艾滋病戒毒人员,不仅厌世,更有比厌世还痛苦的绝望感。表现在不愿意与人接触,会互相挑衅,不积极锻炼。
岳山初来时也是这样,据戒毒所里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介绍,他一开始显得很孤僻、不合群,特别是得知自身已经被HIV感染后,晚上经常迟迟不能入睡,影响其他戒毒人员休息,与其他戒毒人员发生争执,互相推打,事后民警对其批评教育,反应异常强烈,不服管教等适应不良的多种表现。
刚入所,没有亲人会见,个人帐上也没钱了,特别是自己在得知被感染上HIV病毒后更是感得自己的人生完了,在入所收治之初就处在一个麻木的生活状态。
反复开展的心理咨询之后,岳山逐渐平静了下来,至少不对生活麻木,他也经常给自己暗示:“我还活着,我要出去。”
戒毒所每月给他们发一些零花钱,岳山会去戒毒所里的小卖部买一些牙膏等用品,当然,这些钱,对于在外面的他,还不及1/3袋毒品,但在这里,足够了。
一年多的心情从伏到起,岳山越来越快乐,高兴地时候,他会将过节分来的苹果送给邻床的小伙子,甚至几个男人躺在床上来上几段“黄段子”偷着乐。
情绪越来越好,岳山说,这有赖于王副大队长和他的同事们。
“被抓破脸”
在一次与艾滋病戒毒学员的较量中,王副大队长“一战成名”。
2008年11月28日早上8点,时任艾滋病专管中队长的王副大队长照例巡查,发现艾滋病戒毒学员陶刚(化名)不服从管理,不起床,他上前去劝导,陶刚猛地一个翻身,用手狂抓警官,后者脸部被抓破,鲜血直流。
这也是该所队两起“流血事件”之一。
被抓破了脸的民警,回到家里才感到后怕
王警官被立即送往了省疾控中心,服药阻断病毒,接受检测。结果乐观,王警官迅速赶回了中队,“想法很简单,我如果不露面了,学员间就会传,中队长都怕了,以后管理更难了。”
而陶刚更慌了神,“糟了,不死也要脱层皮。”
事实并非陶刚的想法,王警官严厉地批评陶:“你已经违法了,再不服从管理,你的后果会是怎样?”留给陶刚一个问号。
而50多号人的中队,迅速对“黑脸队长”及管教民警肃然起敬,至今未再发生“挑衅”事件。
王警官说,回到家里,感到后怕,但不敢告诉家人。
之后数月的几次检测,均告无恙后,王警官和同事、领导都放下心来。也因为连续在艾滋病专管中队一线的努力,他被司法部评为全国监狱劳教工作模范个人。
第二起“流血事件”发生在去年夏天,一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在洗漱间不慎跌倒,前额重重地撞在水池边上,血流不止,地上也一摊子血迹,值班的民警小龚一个箭步上前,先用白毛巾按住伤口止血,随后于同事一起将该戒毒人员送到所医院包扎,小龚面对感染艾滋病的担心,一笑了之:“这些常识我都懂,当时事态紧急,人命关天,管不了这么多了。”
一线劳教民警的“职业暴露”风险很大,不能有万一,压力很大。许多管教民警还瞒着家人,也不敢告诉朋友自己的具体职业。
流传在管教民警嘴里的一句话来自一名学员,却也实在地反映劳教民警的工作性质:“我是有期的,你们是无期的。”
九名干警,六个已婚。夫妻间尽量避免谈论工作的话题,去年,孟警官女朋友知道了他工作性质后,闹了别扭,感情越来越淡,之后分手。85年出生的徐警官,也谈了女朋友,但还没敢向女朋友“交代”与跟她每天相处时间一样长的自己直接管理的对象。
新一届所党委班子成立后,更加高度重视和关心专管中队民警,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在征得省劳动教养管理局党委的同意后,在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疗休养、岗位补贴等方面给中队管教民警以“特殊”的待遇。
年轻的管教民警们同样期待被认同
事实上,有许多民警是主动要求进入该中队的。现任中队长倪展文即是其中一位。他说,数年前,自己哪怕夏天,都要带着面罩见戒毒人员,每天洗手20多遍。
“这可以理解,谁都担心。”随着常识的增进,以及与戒毒人员的交流熟悉,慢慢地放下包袱,9名中队干警全部脱掉防护服,直接面对面零距离管教,“除去睡觉和午休时间,每天至少12个小时与他们在一起。”
为了不出现一起事故,劳教民警想了许多办法。甚至不讳言“耳目”,在这个小圈子里,也有“帮派”,以来自地域划分,一次,两派有点矛盾,很可能演化为斗殴。“耳目”迅速传来情报,中队民警迅速分开两拨人谈话,将“火药”熄灭。
在中队,民警重点考虑地是艾滋病劳教人员在“4号楼”因思想情绪不稳可能进行的自伤自残或者自杀事件,对铁器的检查特别细,一个可佐证的细节是,在每次用餐之后,民警会严格清点汤匙的数量,严格收回。
这个中队很特殊,“一流血,后果不堪。”倪中队长说。
在某种意义上,与艾滋病患者同样期待不歧视、被认同的,还有倪展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管教民警们,他们平均年龄仅仅27.7岁。
李孟春所长说,这些管教民警像极了荧屏上热播的间谍战中的“地下工作者”,因为这是他们心中深藏着“不能说的秘密”。
浙江经验正在被复制
去年“12.1”国际艾滋病日,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劳动教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吉永根专程到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慰问艾滋病专管中队全体民警、看望艾滋病戒毒人员,并询问了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生活、学习、医疗情况,并勉励他们要好好接受教育矫治,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增强生活的信心。
在4号楼,伙食标准比一般常规学员要高,医疗全部公费,病发后免费服用药品,解除劳教后还可获得300至500元不等的路费。
一周还有两天休息,这个时间学员们可以通过挂在墙上的一部蛋黄色的“亲情电话”与家人报平安。
但“艾滋病”,是电波里唯一被过滤的关键词。对其社会关系网,省强制隔离戒毒所采取了“隐私保护”。但对具体学员,则进行了应该的公开告知。
2003年,“双公开”的大胆举措
2003年12月8日,浙江正式收教第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派出所民警回忆,那时候戒毒人员是被“五花大绑”送到这里。
他们以为自己有艾滋病,犯了事会被放走,万万没想到要劳动教养。
当时处境确实尴尬,其时,艾滋病犯罪是个新课题,一开始全国不成文的做法是,因犯罪抓获的艾滋病人,一律刑拘后放掉,由于艾滋病犯罪一段时间的猖獗,之后对这一群体采取了收押服刑,但也是不公开,直接混合管理。
双公开对应的,是“盲管”。不单独集中管理,会出现许多潜在的威胁。比如同性恋、打架会不会传染到其他服刑人员?
2003年起,浙江劳教场所第一个开始单独集中管理,并“双公开”。当年,一份由省政法委等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打击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出台。
所谓“双公开”,即通过初检复检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的戒毒人员的,第一时间由所队或疾控专家面对面通报病情;另是对场所内管教民警和其他服刑人员公开,这里有艾滋病患者。
而艾滋病患者,被充分告知后,自己也有个接受过程,在接受中,民警给予人性化管教,增强其生活的自信。
握握手,你也能给他力量
罗爱民政委对记者说:“在管理这个特殊群体的过程中,专管中队民警的确不容易,承受着职业暴露、家人担心受怕、他人的困惑疑虑乃至冷嘲热讽等多重压力,但中队民警做到不歧视、不放弃、不抛弃,在生活上关爱他们,从精神上鼓励他们,帮助他们重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浙江经验正在被复制,全国越来越多的省份来学习,并开始对这一特殊群体单独管理。
劳教民警们更希望全社会形成共识,用“心”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让飘动的红丝带连接你我、牵动世界,让这个特殊群体在没有歧视的环境中受到应有的尊重、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至少社区里碰到了一位认识的艾滋病感染者,你愿意伸出手与他(她)相握,并给予他(她)力量。
相关链接
相关阅读青岛新闻
- 06-08·基本药物年底全市覆盖 将免费为孕妇筛检艾滋
- 06-05·与卖淫女发生关系 海归男子疑感染艾滋欲轻生
- 05-13·东莞艾滋阴云不散 力争让85%小姐都用安全套
- 04-29·女星遭父亲曝料染艾滋 17岁与老板上床(图)
- 04-28·男子自知患艾滋与人性关系 被诉危害公共安全
- 04-10·河北艾滋女事件制造者因毁谤罪获刑三年(图)
- 03-24·钟南山:半数国人携结核杆菌 暴发危害超艾滋
- 01-30·女子险遭强奸急中生智 大喊我有艾滋逃过一劫
- 01-20·女星称得艾滋传染500男人 引范围恐慌(图)
- 01-20·色情明星称将艾滋传染500男人引大范围恐慌
- 01-15·因为艾滋 我没法把爱字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