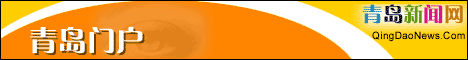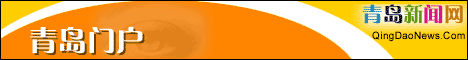|
刘光溪――入世就是加入世界经济的主流
整整13年,中国至少有6次似乎看见了WTO的曙光,但是黎明总是没有到来。这一次,天真的快亮了,中国已经站在了WTO的门槛。
前不久,被称为中国WTO“第一博士”的刘光溪先生来到青岛,作了题为“入世与青岛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演讲。演讲之后,记者在海天大酒店采访了他。略显秃顶但实际十分年轻的刘博士侃侃而谈……在中美双边谈判中,美国人追问得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是政府说了算,还是企业家说了算?中美双方13年谈判中,仅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就谈了6年记者:中国入世一波三折,前前后后经历了13年,这在WTO的谈判中是没有过的。您认为这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原因还是西方国家有意设置障碍?
刘光溪:中国入世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从客观上讲,这十几年中,中国始终在变化,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化,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及对世界影响的变化。国际经济秩序也在变,美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经济的成长或衰退,随时改变着世界经济贸易的格局。与此同时,从复关到入世,世界贸易组织从单纯的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范围和内容要比以前大得多。而且这三个变化很难找到一个磨合点,这就决定了中国入世的复杂程度。
入世这两个字,就是中国加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这个主流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了几千年,建国以后又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仅仅有9年的历史。在谈判过程中,我们曾给美国人讲“有计划商品经济”,但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结果问题不是越谈越少,而是越谈越多,1个问题变成了3个问题。总体上看,入世谈判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当中国改革取得进展,谈判就顺利;当中国改革受阻,谈判就越发艰难。
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实际上体现了官本位与企业家本位的冲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谈判核心就是遵守规则和市场开放,这要求我们的经济决策者不搞黑箱操作,各项决策要有充分的透明度,还要统一行事,不能搞政出多门。而最重要的是要严格划定政府的行为,把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改成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事实上,直到党的十四大召开,中国正式宣布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从而获得了入世的体制条件。
记者:刚才您说到从复关到入世,世贸组织的范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竟有那些变化?
刘光溪:如果说关贸总协定只是协调货物贸易管理的话,世贸组织在1995年1月1日取代关贸总协定以后,它的职能大大地拓宽了。这个职能拓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过去协调货物贸易逐渐扩展到协调服务贸易、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里面主要是冒牌货贸易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从过去单纯的协调和管理规范边境措施,逐渐转向到市场壁垒。边境措施是什么?就是关税和非关税,通过关税来调节进出口,通过非关税措施来控制进出口、管理进出口。这个转变的影响是很大的,过去我们只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调节,现在我们在进口某一项产品的时候,随着关税水平的普遍降低,单纯用关税和非关税来调节进出口的作用逐渐降低。现在每一个成员都把协调进出口、管理外资政策通过国内的决策部门、立法部门,上升到立法和决策的高度。
过去单纯的成员之间来协商解决某一个问题,现在逐渐过渡到需要跟国际上某一个领域的有管理职能的多边经济组织进行协商和沟通。比如货币汇率方面的政策,需要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协商解决;信贷和发展政策问题,需要跟世界银行进行协商解决;知识产权问题,需要跟联合国的知识产权组织进行协商解决。所以说,世贸组织的影响,通过职能的扩大在慢慢提高。
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块试金石,如果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很完善,预警机制很完善,它对你不会产生坏影响的。所以当经济全球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冲击的时候,是因为其本身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存在很大问题记者:现在社会上关于WTO的说法很多,您能否对WTO作一个简单的描述?
刘光溪:关于WTO,上到政府官员,下到企业主管,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在谈论。各种各样的说法多了,有些很离谱。比如有些人认为WTO无所不能。这就是一种误解。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比差别很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它的决策程序是靠董事局。世界银行是根据你的捐款、出钱以及用钱的多少,由21个成员组成董事局,行长在信贷管理、资金流向方面有一定的实权。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只有500来人,仅仅是个“秘书班子”,就是一个会议的组织者、谈判的组织者,它本身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
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有准司法效力,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国内有好多部门非常忧虑,认为我们一旦入世以后,世贸组织好象就会对我们中国的司法、立法产生多么大的约束和规范。约束和规范是肯定要有的,但它到底约束到什么程度,力度有多大,很值得研究。比如美欧之间的香蕉案子,欧盟败诉后就是不实施,美国就想找别的方面、通过别的渠道来制裁它。但是这个制裁和反制裁之间的关系在成员政府面前也经常显得很苍白。所以不要把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看成有多么大的强制力。世贸组织发展到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其能充分尊重成员政府的决策主权和国际面子。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格局下,归根结底,还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是主流,还是双边关系发挥重大的作用,说白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现在社会上一些人对WTO感到恐惧,主要是担心外国企业会挤垮本国企业,您对此怎么看?
刘光溪:这种担心主要是因为人们对WTO还不了解。世贸组织不是一个超国家的经济组织。就拿成员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制定的基本规则和准则来说,每一个成员都毫无疑问应该实施和履行承诺。但是如果说在某一项承诺方面,一成员国内政治层面有压力,或者说某一个行业有现实困难,很难在承诺期完全到位,该成员可能就提前告诉世贸组织有关委员会。
比如像我们承诺汽车工业品的关税到2006年降到25%,如果说到了2003年,一看汽车工业降税速度快了点,对本身汽车工业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政府完全可以照会世贸组织秘书处,说我们承诺到2006年降到25%,但是现在很难实现这个目标。世贸组织会派专家来考察,跟你协商,绝对会尊重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不会强迫中国政府必须履行你的承诺。
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原则当中有例外,例外当中有原则,一环扣一环,绝对不会让每一个成员因为加入了世贸组织而影响其正常发展进程。它允许一个成员可以保留使用关税和价格因素的保护手段。这个价格因素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通过数量的配额、数量的指标来影响正常的贸易,但允许使用通过关税,通过关税的上限约束和下限约束,通过关税配额的管理方式。世界贸易组织并不是让你完全缴械,放弃任何保护手段。关税水平大幅度调低,配额、许可证以及法定的商检慢慢地开始调整以后,成员政府还可以通过立法的方式,通过质量认证、环保、绿色标签、动检、植检、卫检等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幼稚产业和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不管市场经济多么发达、市场功能多么完善,动检、卫检和植检是必须要保留的,这是主权的象征。经济全球化是块试金石,如果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很完善,预警机制很完善,它对你不会产生坏影响。所以当全球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有冲击的时候,是因为其本身经济结构和经济改革存在很大问题。中美入世谈判,与其说是一场经贸谈判,不如说是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大碰撞。两种文化价值趋向、两种理念的碰撞、冲突,通过这场经济贸易谈判反映出来。这种矛盾的交锋、冲撞和磨合,对中华民族价值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理性思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记者:中国为入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WTO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刘光溪:世贸组织的安全基础是争端解决。之所以有世贸组织,是因为人类还没有达到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理想境界。自由贸易再好,当一个主权政府、一个国家(地区)在面临国内政治层面压力的时候,都要采取保护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措施。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中美之间发生贸易上的纠纷,美国就可以利用其国内1988年综合贸易法案里面的特殊301、超级301条款来制裁中国。一旦打起贸易战,双方实行起报复与反报复,双方的损失都会很大。如果加入了世贸组织,双方争来争去最后还是要走向日内瓦,而不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正面的交锋、冲突。中国参加世贸组织一个主要的考虑,就是通过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来维护和稳定中国对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这对中国这个文明历史比较长、历史沉淀比较雄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世贸组织的这个安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能推动一个成员慢慢地由多边的争端解决来取代双边的争端解决方式,这有利于维护一个成员对外环境的稳定。
记者:中国不加入WTO行不行?中国入世的意义恐怕不止于此?
刘光溪:中国入世的意义完全可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相比。中国经济改革目前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别的办法已经难以推动。过去是改革促开放,现在是开放促改革。中国封闭了几百年,排外心理影响不小。因此,难对付的并不是美国人,最难的是与国内各行业各部门的代表谈判。中国加入WTO一直被形象地称为“狼来了”,接受削减关税、降低保护等要求也大都被说成是中国政府作出的“让步”和“牺牲”。实际这样做不是让步而是进步,不是牺牲而是贡献,不是超前而是补课。比如,进口车的关税10年前就该降到25%了,我们已整整滞后了20年。否则,中国的老百姓就可以用1万美元买到进口豪华车,而不是用2万美元买国外二级市场上的淘汰车。
WTO就是规范国与国之间那些违反市场经济行为的。中国入世的过程就是一场市场经济基本知识的普及教育。WTO的一套规范,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是客观存在,是几百年来发达的市场经济积累形成的一套文明的成果,你得大胆去吸收和借鉴。不要再去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世贸组织是对我好还是坏了。石头已经摸到,就看过不过河了。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对我们民族是思想的启蒙,即按照理性、按照规则来行事。其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能再混下去了”,消极对抗才是最可怕的。
另一方面,中美入世谈判,与其说是一场经贸谈判,不如说是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大碰撞,其中有意识形态的,也有人文价值的,而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只会是暂时的,人文价值上的冲突却是永远的。两种文化价值趋向、两种理念的碰撞、冲突,通过这场经济贸易谈判反映出来。这种矛盾的交锋、冲撞和磨合,实际上对中华民族价值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理性思维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WTO生命力源自广泛的基础,就是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成员不能把自己的任何意志凌驾于另一个成员之上。不管你多么强大,如果投票的话你只有一票记者:有人说WTO既然是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各方面还没有准备好,加入这个俱乐部,是不是要受欺负?
刘光溪:中国发展了5000年,还没有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呢?再过50年能准备好吗?到那时,即使准备好了,也将失去入世的意义。实际上,在WTO成员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才加入的。
世贸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管理、有协调的贸易,不是一种完全放任自流的贸易。1985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一个声明,说美国今后不再倡导自由贸易,而是倡导公平贸易。这个公平贸易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开放,我就对你开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从自由贸易到公平贸易的转变影响可是太大了。WTO生命力源自广泛的基础,就是任何时候不是按哪一个成员政府的意志或受其影响,大家要坐在一块共同探讨,实现协商一致,来制定共同遵守的规则。世贸组织的议事基础是协商一致。任何一个成员不能把自己的任何意志凌驾于另一个成员之上。不管你多么强大,如果投票的话你只有一票。
现在有些人喜欢用“利弊”来分析中国入世的问题,我认为利弊分析大有局限。因为现在的“利”可能就是将来的“弊”,而人们普遍认为的“弊”无非是因此而带来的压力,很有可能转化为将来的“利”。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无所谓利弊,中国入世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从近期看,有助于加速改革;从中期看,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从远期看,有助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早入世,就是中国最大的根本利益,没有比这更大的利益了。
记者:世贸组织的运行基础是规则基础,WTO有那些规则?
刘光溪:在世贸组织的出版物里面,世贸组织的基本规则有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贸易渐进自由化原则、例外原则等等。这些基本规则贯穿于世贸组织21个协议。
世贸组织的大部分规则都是我们过去不熟悉的。比如透明度原则,就是每一项法规出台之前,不仅要广泛地征求国内有关部门和企业的意见,现在还要加上国外同类行业、跨国公司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再比如统一实施的规则。对我们这个条块分割了这么多年的国家来说,怎么确保统一实施呢?只能有统一的市场基础才能有统一实施,如果说搞诸侯经济,田到地头死,货到地界死,那就完了。所以有的国家与我们进行入世谈判时,别的不很担心,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入世以后,国内各个省市自治区的贸易政策的统一性、关税政策的统一性和立法的统一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履约问题。我很赞成这样的观点:中国要加入WTO,首先要把国内的WTO做好。这里面有三层意思:第一,将要对国外开放的领域,对国内同类行业还不开放,何谈培养自己的竞争能力?电信、保险等等行业都是例证。第二,就是政策的趋同性。按所有制把企业划分为民营和国有,其相关政策也不一样,谈何公平竞争?第三,就是立法方面的调整。所以统一实施的问题,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认识和行动,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怎样应对WTO。条块问题是长期遗留下来的,是制约中国国内经济市场趋同性最大的障碍。入世对于企业家的影响是间接的,而对政府行为的影响是深远的。要遵守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让官本位向企业本位让路,政府的任务只是建立自由、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让大家参与其中记者:中国入世后,企业、政府扮演的角色将发生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刘光溪:中国入世,政府部门首先要入世。政府部门不入世,我看企业家的日子跟过去一样很难过。在中美双边的谈判中,美国人追问得最厉害的就是我们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是政府说了算,还是企业家说了算?入世首先应对的是我们各级综合管理部门,而不是企业家。
第一,世界贸易组织任何一个条款,都没有涉及到企业的行为。企业行为不是世贸组织所规范的,只要把政府的行为规范好了,企业的行为理所当然就规范好了。什么样的体制创造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培养什么样的企业家。这是实践已经证明了的事实。第二,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我们在今后的3年、5年或10年里慢慢地理顺了经济管理的运行体制,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自然就相应建立起来了。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早在300年前就讲到了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发挥很大作用。通过世贸组织的一套规范和成员的监督,把我们经济管理部门这只看得见的手大大的收缩,大大的规范,那么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手舞足蹈”了,企业家的环境就灵活了、宽松了。
市场经济是法制基础上的信誉经济,加入WTO将帮助我们建立规则、章法之上的信誉。我们一方面要让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同时要斩断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实现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提供信息和服务,它和企业的所有关系应该仅为税收关系。
刘光溪简历:1964年1月3日出生,山东五莲人。2001年入选当代中国“十大新锐青年人物”。1981年至1988年就读于山东师大外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文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6年成为国内第一位“WTO与区域经济合作”专业博士生。
从1988年开始,刘光溪就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的谈判工作,曾任外经贸部国际司WTO处处长。1997年担任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的特别助手。1999年被任命为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商务参赞。2000年调任上海WTO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副院长。
刘光溪发表论文100多篇。著作有《互补性竞争论:区域集团与多边贸易体制》、《中国与“经济联合国”:从复关到入世》等,其中《互补性竞争论》获得1996年度国际贸易学术最高奖―――“安子介国际经贸研究奖”优秀著作一等奖。
(青岛日报
2001年7月28日)
|